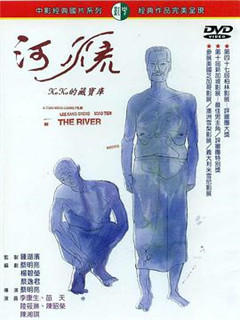- [ 免費 ] 第1章 河與沙漠
- [ 免費 ] 第2章 母親的不適
- [ 免費 ] 第3章 新的壹天
- [ 免費 ] 第4章 調查
- [ 免費 ] 第5章 壞消息
- [ 免費 ] 第6章 草原上
- [ 免費 ] 第7章 水文站
- [ 免費 ] 第8章 陸伯伯
- [ 免費 ] 第9章 水
- [ 免費 ] 第10章 新聞人物
- [ 免費 ] 第11章
- [ 免費 ] 第12章
- [ 免費 ] 第13章
- [ 免費 ] 第14章
- [ 免費 ] 第15章
- [ 免費 ] 第16章
- [ 免費 ] 第17章
- [ 免費 ] 第18章
- [ 免費 ] 第19章
- [ 免費 ] 第20章
- [ 免費 ] 第21章
- [ 免費 ] 第22章
- [ 免費 ] 第23章
- [ 免費 ] 第24章
- [ 免費 ] 第25章
- [ 免費 ] 第26章
- [ 免費 ] 第27章
- [ 免費 ] 第28章
- [ 免費 ] 第29章
- [ 免費 ] 第30章
- [ 免費 ] 第31章
- [ 免費 ] 第32章
- [ 免費 ] 第33章
- [ 免費 ] 第34章
- [ 免費 ] 第35章
- [ 免費 ] 第36章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8章 陸伯伯
2018-9-27 20:33
連著幾天,於幹頭他們都來。來了就咋咋呼呼,像是野灘裏的牦牛,灑脫得很。
鄧朝露已經聽說,這些人早就是路波的常客,他們跟路波稱兄道弟,關系親熱得不是壹般。來了吃路波的,喝路波的,抽路波的,走時還順手牽羊,將水文站壹些七零八碎的東西拿走。在他們眼裏,水文站就是路波的。水文站的職工有意見,但礙著路波是元老,都不敢說。路波自己也不檢點,對這些人尤其縱容。他現在精力根本不在工作上,對站上的事想問了問幾句,不想問什麽也不問。幸虧副站長是位很敬業的同誌,事無巨細都替路波把心操了。上級念著路波是位老同誌,馬上到退休年齡,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反正現在工作就這樣子,沒誰真拿水文站當回事。
鄧朝露聽了,心裏越發不安。怎麽會這樣呢,在她心目中,母親他們這壹代人,沒有壹個不敬業的,工作起來個個玩命。就算是苗雨蘭阿姨,也是壹個工作狂。獨獨路伯伯,變成了這樣。
路伯伯這是怎麽了?
第三天,那個叫於幹頭的再來,鄧朝露就堵住了他。
“妳找我路伯伯幹什麽?”
於幹頭撓撓頭:“妳是小露吧,妳媽我們認識的,是管理處處長對吧?妳光屁股的時候,我還抱過妳呢。”
鄧朝露差點呸出壹聲,厭惡地瞪住這個人:“我路伯伯不歡迎妳們,這裏是單位,不是草原,妳們以後少來。”
於幹頭這才明白,鄧朝露截住他是為了表達不友好,而不是歡迎他,搓搓頭道:“這妳說了不算,我們找妳路伯伯是商量大事,大事妳懂不?不懂吧,關系到這條河,關系到整個流域。這事妳不用管,我們會奔走的。”
“奔走個鬼啊,我求求妳們,放過我路伯伯吧,他有病,經不起折騰。”鄧朝露眼淚都要出來了,這兩天她看到路伯伯在大把大把吃藥,咳嗽起來很厲害,每次吃飯都很少,夜裏也是半夜半夜地睡不著覺。昨天半夜他又在吹笛了,笛聲淒婉,直往人的心裏鉆,攪得鄧朝露根本就沒睡。
“嘿嘿,妳這丫頭,話咋這麽說哩,有些事妳不懂,甭看妳是研究生,社會上的事妳還真不懂。算了,不跟妳多說,妳路伯伯呢?我找他有急事。”
“他不在!”鄧朝露沒好氣地給了壹句。於幹頭並不介意,沖院裏“老路”“老路”喊了幾聲,路波就像壹頭老牛壹樣奔了出來。他們不願意讓鄧朝露聽到談話內容,又往聽山石那邊去。鄧朝露走過去,壹把拽住路波。
“憑什麽啊,不跟他們來往行不?”
“這妳不懂的,回去!”路波嚴肅起來。
“我不,我讓妳回去,不許跟他們來往。”
“亂說什麽,快回去。”路波臉色變得難看,不滿地看著鄧朝露。鄧朝露偏不,任性地站在那裏。這時副站長出來了,沖鄧朝露說:“到我辦公室去吧,我有話跟妳說。”
副站長不是本地人,華東水利學院畢業後分配到了祁連省,畢業時間跟鄧朝露差不多,鄧朝露讀研,他沒讀,現在也是祁連省水文領域的中堅力量了。他跟鄧朝露推心置腹談了壹下午,從河談到流域,談到流域這些年的治理,還有地方政府或省裏出臺的種種舉措,以及下遊和上遊不可調和的矛盾。兩人似乎有很多共同語言,看法也基本壹致。不過對流域的未來,鄧朝露充滿憂慮,副站長卻淡淡壹笑,很有信心地說:“壹切都會好起來的,只是時間問題。”
“官僚,妳們這些人就愛說官僚話。”兩人年齡差不多,副站長大鄧朝露幾歲,資歷也不相上下,鄧朝露在他面前說話相對從容壹些。副站長並不爭辯,這是壹個看上去城府頗深的人,心裏能藏住東西。他憂傷地捋了下頭發,話題落到了路波身上。他問鄧朝露,是不是對路波很失望?鄧朝露嗯了壹聲,副站長笑笑,說了聲別。鄧朝露問為什麽?副站長嘆壹聲,搖了搖頭,很是沈重地說:“我也說不清,看到站長那樣,我很自責,總覺得是自己沒把工作做好。”
“跟妳有什麽關系啊,妳替他做的已經夠多了。”鄧朝露不解地說。
“有些事沒有因果,有些事卻必有因果,路老師他心裏苦啊。”壹席話說得兩人都垂下頭去,半天,副站長說:“不要對站長有誤解,我雖然不知道他在做什麽,但我相信,他是正確的,他絕不是壹個自暴自棄自私自利的人。”
“正確?”鄧朝露驚訝了,站起身子,還以為副站長叫她來,是要商量辦法拯救路伯伯,沒想他居然說路伯伯是正確的。
“他正確在哪,就這樣天天跟這些人在壹起,妳看他現在過的這叫什麽日子!”
鄧朝露激動了,壹氣說了許多,言語中甚至有傷害的字眼出現。她詛咒那些穿戴不整的人,詛咒於幹頭也詛咒五羊,說他們是無賴,壹夥遊手好閑好吃懶做的人,是他們讓路伯伯墮落,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
副站長默默聽著,並不打斷鄧朝露。等鄧朝露說完,起身,望向窗外,望著對面茫茫的祁連。
良久,他說:“我們的目光還是太淺了,看不透這座山,看不透這裏的人,等著吧,他們或許會創造奇跡。”
鄧朝露聽得莫名其妙。回到路波辦公室時,路波睡了,他喝了不少酒,臉紅著,呼吸聲很重。再去看時,於幹頭他們已經走了,聽山石下壹片幹凈,什麽痕跡也沒留下。鄧朝露有些茫然,孤獨地坐在聽山石上,遠處的松濤聲傳來,轟擊著她的心。河水嘩嘩,世界進入完全陌生的狀態,鄧朝露忽然哭了,她不知道為什麽要哭,但她確確實實哭了。哭到後來,偏是又想起那個叫秦雨的人,想起自己死去的愛情。她幾乎要被痛苦淹沒了,感覺自己已被這個世界拋棄,誰也不在乎她,誰也不跟她講實話,誰也在拒絕著她欺騙著她。
這天黃昏,天將要黑下來的時候,路波非常鄭重地將鄧朝露叫到面前,跟鄧朝露談起了秦雨。這是路波第壹次跟鄧朝露談愛情,場面顯得神聖。愛情兩個字,在路波心裏的地位跟別人斷然不同,路波這輩子對什麽都無所謂,他過得隨心所欲,無欲無剛,臉上讓歲月這把刀深深地刻下壹蹶不振四個字,到哪都洗白不了,很難從他身上看到令人怦然心動的東西。獨獨對愛情,路波卻有頑固的眷戀和奉若神明的虔誠。鄧朝露對秦雨那點心思,路波早就知道了,所以沒點破,是想讓兩個年輕人自自然然戀愛,他等瓜熟蒂落那壹刻。人活著有愛情多好啊,再暗淡的人生也會因此而精彩,再虛弱的人也會因愛情而剛強。哦,愛情,每每看到有人相愛,路波自己先陶醉起來。沒想到這事突然有了變故,黃了,沒了,夭折了,半途而廢了,路波心裏不好受啊,感覺心上肉被人狠狠挖掉了壹塊。
鄧朝露起先躲閃著,不肯說實話,任憑路波怎麽問,只說哪有這回事啊,路伯伯,我跟他之間啥也沒有,真的沒有。路波急了,擡高聲音說:“小露妳別打斷我,伯伯就妳這麽壹個閨女,妳的心思伯伯懂,伯伯所以不提這事,就是不想讓妳難過。”
“我沒難過。”鄧朝露忽然捂住鼻子,不爭氣的鼻子,居然就酸酸地發起了澀,後來又忍不住發出壹片嗚咽。
路波心疼地伸過手,攬過鄧朝露的肩說:“不難過,小露不難過。”可他自己的眼淚卻下來了,竟然哭得比鄧朝露還恓惶。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麽傷害比愛情帶來的傷害更深重呢,沒有,路波堅信沒有。愛情可以讓壹個人幸福地活,活得奪目,活得燦爛,更可以讓壹個人死。他算是死過好幾回了,如果不是心中還藏著壹個結,怕是早就壹頭紮進雜木河了……
哭了壹陣,路波抹掉淚說:“小露,告訴伯伯,還有辦法挽救不,只要有壹線希望,伯伯就豁出去,為妳赴湯蹈火。”
鄧朝露感動地望著路波,這句話好溫暖哦,幾乎可以撫平她內心的傷。她堅定地搖搖頭,她不是那種企求別人施舍的人,更不是從別人手裏掠奪幸福的人。這點上她跟母親鄧家英是那麽得像,跟路波也是驚人的相同。他們三個,真是像壹家人哦,可惜不是。
“不,伯伯,您別枉費心機了,死去的東西再也不會復活,不會。”她咬住嘴唇,咬得嘴唇都已出血了。血從牙縫裏滲出來,滴在路波心上,路波的心銳利地疼了幾下,攬著她的手禁不住發抖。這是壹個多麽懂事的孩子啊,又是壹個多麽堅強的孩子,路波還怕她挺不過來呢,更怕她做出什麽荒唐事。
女人是為情生為情死的,這點路波非常堅信。路波幾乎就要欣慰了,可心的某個地方突然壹動,柔柔軟軟地那麽動了壹下,就又把他動得復雜,動得恍惚,仿佛心裏糾結著的那個結猛然要打開。他已經感覺到攬著鄧朝露的手跟剛才有些不同,傳遞出另外壹種力量了,慌忙間他將自己制止住。
不能啊,他聽到這麽壹聲,手陡然壹松,從鄧朝露肩上落下。
路波捂住了臉,壹股藏在心底很深處的淚噴出,差點將他淹沒,差點將他帶進另壹股洪流中。半天,路波平靜下來,變得不那麽神經。他沖鄧朝露笑笑,盡管勉強,但溫暖是顯而易見的。
“忘掉他吧,伯伯不忍心看妳這樣子。小露這麽優秀,還怕沒男孩子追,將來壹定找個白馬王子。”
鄧朝露撲哧壹聲笑了,路波這麽老舊壹個人,居然也能說出白馬王子。她仰起脖子說:“伯伯妳甭替我擔心,妳的身體要緊,以後不許喝酒,跟那些人還是少來往。”
路波淡淡地笑了笑,說:“他們是好人,伯伯信得過他們。”
“可我信不過他們。”鄧朝露頂了壹句嘴,轉而又甜甜地笑了。因為她看見明亮的笑已在路波臉上升騰起來。她這次來,不想給路伯伯心裏添堵,只要路伯伯開心,比什麽都重要。於是起身,高高興興替路波洗衣服去了。白天裏她還賭氣,路波臟衣服堆了壹堆,本來想洗的,後來故意裝看不見。這陣就笑自己傻,有些氣妳根本賭不出,也不該賭。路波癡癡地盯著鄧朝露的背影,盯著盯著,就又恍惚,不自禁地就又想起壹些事來,後來他嘆壹聲,回頭拿出相夾,壹遍遍撫摸。
鄧朝露本想在雜木河水文站多待些日子,她有個課題,需要石羊河近壹年的水文觀測數據,她想借這個機會,把數字整理全。副站長已經答應,讓站裏幾個年輕人幫她。誰知第二天,山下就出事了。當時鄧朝露正跟幾個工作人員翻觀測記錄,壹項項往表上抄錄數據,忽聽得門外響起尖厲的聲音,是那個叫五羊的,進院就喊:“老路,老路站長,快出來!”鄧朝露擡頭往外看,就見路波急急地走出辦公室,跟五羊在院裏嘀咕幾句,然後坐上五羊的摩托車走了。鄧朝露感覺不大對勁,追出來,路波他們已沒了影。正生著氣,身後響起副站長的聲音:“走吧,今天壹定有熱鬧看。”
鄧朝露坐著站上的車,跟副站長他們壹同到了離水文站十公裏遠處的南營水庫。這是石羊河從源頭數起的第壹座水庫,雜木河還有紫水河以及南部山區的幾條河流在南營前面的貢達梅嶺匯合,然後滾滾而下,要穿過雄險的野鹿谷時,突然被壹座大壩攔住,這大壩就是南營水庫。
這座水庫跟西邊另壹條支流上的西營水庫、東邊黃羊河的黃羊水庫構成石羊河第壹道防護體系,活生生地將奔騰的河水給攔斷。也正是憑了這三座大壩,上遊谷川區才儼然成為河的主人,像是掐住了河脖子,總是顯得底氣比別人足。鄧朝露他們趕到的時候,下遊龍山和沙湖的人剛剛跟南營這邊的群眾打完架。兩邊來的人都不少,尤其南營,近乎把半個鄉的人都發動了上來,黑壓壓地站滿了大壩,兩邊山坡上也是。而龍山和沙湖那邊自然就顯得力量單薄了些,他們來了三卡車人,是來搶水的。
鄧朝露急著找路波,生怕路波攪進是非中。副站長讓她別急,壹再說路所長不會的。可他顯得比鄧朝露還急,已經不停地跟別人打聽路波的下落。圍過來的人很多,七嘴八舌都在說剛才打架的事。有人說打得很兇,龍山那邊兩個人斷了胳膊,另壹個被打斷了三根肋骨。也有人說屁事也沒,都在幹吼卻不動手。說這話的人中就有於幹頭他們。他們看上去幸災樂禍,幾個人圍在壹起抽煙。那煙肯定又是路波賞給他們的。鄧朝露心裏就想,這架跟路波有關,壹定是他在背後教唆,讓於幹頭們挑弄是非。後來得到的消息果然如此,路波充當了幕後教唆和操縱者,於幹頭們不過是他的“幹將”。往下遊調水是谷水市早就做出的決定,鄧朝露他們在沙湖縣搞完那次科研,谷水市的決定就做出了。上遊谷川區卻堅決不答應,幾次協調都沒成功。但下遊旱情壹天重過壹天,不只是莊稼,樹也成片成片地渴死。沙湖縣幾度告急,孔縣長擺了好幾次酒宴,就為了讓谷川區的領導點個頭。可這個頭點起來實在困難,大家都盯著這點可憐的水,盯著這條可憐的河,僧多粥少,顧及不到啊。僵來僵去,市裏發了火,強行要求上遊谷川區開閘放水,解下遊之困。誰知開閘第壹天,就遇到了上遊群眾的圍攻。
南營鄉幾千號人站在大堤上,打著橫幅:人在水在,誓與河水共存亡。下遊沙湖和龍山的群眾也打起了橫幅:壹河所生,壹河所養,有難同當,有福共享。有人甚至打出了“娘的奶頭妳吃得我也吃得”這樣直白的標語。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區裏和縣裏的領導都被叫去,谷川區長不講話,只是說只要群眾答應怎麽都行,我們沒意見,都是壹河水養大的嘛。龍山縣長說這不是明擺著推責任嗎,群眾說了算還要領導幹什麽?谷川區長笑說,依靠群眾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這個傳統什麽時候都不能丟。龍山縣長明知人家是在搪塞,不想解決問題,但又在語言上占不了優勢,只能焦急地看沙湖縣長孔祥雲。反正沙湖旱情比龍山還重,只要沙湖能度過去,龍山就能度過去,好歹龍山還有幾座水庫呢。孔祥雲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他以前在谷川做過常務副區長,去年才調到沙湖縣。上遊情況要說他比龍山縣長更了解,三座水庫的水充其量也只能解決谷川自己的問題,但他現在是沙湖縣長,就不能這麽想問題。他站出來說:“聽群眾的沒錯,但這條河不是谷川區的吧,祁連山不是谷川區的吧,上遊要豐收,總不能把下遊餓死,怎麽著也得分壹瓢給下遊解渴。”
“水就在庫裏,我沒藏起來,兩位縣長要多少,只管拿走,我絕沒意見。”谷川區長依舊不急不躁地說。
“怎麽拿?妳讓水庫工作人員躲起來,大壩又讓群眾占著,我們怎麽拿?”龍山縣長咄咄逼人道。剛才是群眾吵架,這陣輪到他們吵了。谷川區長卻不想吵,做出壹副甘拜下風的樣子:“我的兩位好領導,千萬別冤枉我,水庫管理人員是讓群眾趕跑的,情況妳們都看到了,再鬧下去,我這個區長也會讓他們趕跑。”
“裝,裝,裝,妳就裝。”龍山縣長明知谷川區長是在演戲,卻又拿他沒辦法,這事攤誰頭上,怕都壹樣。去年沙湖縣跟他告急求援,他壹樣裝了啞巴,壹滴水也沒支援。沒想到同樣的難題現在又擱到了自己頭上。
三位領導都是位子上的人,平時見了壹個比壹個熱情,壹個比壹個客氣,禮尚往來,客套得很。這陣為了水卻要紅臉,也實在是難為他們。
市委書記吳天亮壹直看著三位,他是中途趕來的,他來的時候,三方群眾正糾纏壹起,中間確也動了手,不過還算克制,沒出大問題,傷的幾個人他看過,都不重。本來他想把公安叫來,後來壹想算了,集體突發性沖突面前,還是保持克制的好。
“說吧老陸,這水到底放還是不放?”吳天亮問谷川區長。
“書記,您也看到了,群眾情緒這麽大,我真是無能為力啊。”谷川區長姓陸,聽見吳天亮問話,苦著臉說。
“我看妳根本就沒想著解決問題,煽動群眾情緒,鼓動鬧事,老陸妳膽子不小啊。”吳天亮拉下臉來批評。陸區長結巴著,他還沒膽子讓吳天亮生氣,但他真沒能力說服外面的群眾。正尷尬著,吳天亮開口了,他沖孔祥雲和龍山縣長說:“先把人帶走,其他問題回去再解決。”兩位縣長面面相覷,極不甘心,但市委書記這樣說了,他們也沒辦法,只能服從。
陸區長倒是松下壹口氣來。
吳天亮又轉向市委秘書長:“路波找到沒,等他多長時間了?”市委秘書長結結巴巴說:“站上說他早就出來了,但現場找不到他。”
“打電話給鄧家英,讓她去找!”吳天亮火了。
這個時候,鄧朝露正在四處找路波。水庫上到處是人,黑壓壓壹大片。有的在看熱鬧,有的在等待更大的熱鬧,更多的,卻是在嚷嚷著水。鄧朝露步子飛快地穿來穿去,哪也不見路波的影子。她問過幾個熟悉的人,都說沒看到。後來她看見幾個跟洛巴穿戴壹致的藏人,想走過去問問他們。那些人站在半山腰間,居高臨下地俯視著這些為水吵得不可開交的漢人們。山腰上不知什麽人在唱《五哥放羊》,嗓子還不錯,淒淒切切的聲音跟山下水庫上正發生著的事很不和諧。鄧朝露剛到山腳下,就聽有人說,路波正跟幾個放羊的老漢“挖牛”呢。
“挖牛”鄧朝露懂,是壹種類似撲克牌的玩法,山裏人管壹種紙牌叫“牛九”,閑時沒事,就靠它打發光陰。鄧朝露走過去,見山腳壹背風處,幾個老漢坐在皮襖上,面前攤開壹張羊皮,路波就在中間,手裏抱著“牛九”牌,正笑瞇瞇地計劃著怎麽讓幾個老漢輸掉。幾個老漢壹看就是行家裏手,根本不服他。有個老漢聲音很大地訓他:“磨蹭什麽,出牌啊陸水文。”
“三老虎!”路波猛叫壹聲,甩出三張Q來,老漢哈哈壹笑,臉上露出得意道:“就知道妳舍不得牌,打對老虎我就輸了,三牛!”路波懊惱地連叫幾聲,騰地起身說:“不玩了不玩了,玩不過妳們。”
壹股子塵騰起,是路波屁股上的土。老漢們不依,剛才贏了牌的叫囂:“正玩興頭上呢,不能走,人家搶水妳慌個啥,去搶好了,反正水遲早要幹掉。”
“誰說的?!”鄧朝露奔過去,不滿地瞪了老漢壹眼,壹把拽過路波:“找妳都找瘋了,還有心思玩?”
“找我做什麽?”路波明知故問。老漢幫腔道:“這是鄧家女子吧,嗯,長大了,長成野丫頭了。”
“妳才野丫頭哩。”鄧朝露學著山裏人的話,搶白了壹句。幾個老漢馬上笑了,都說:“像,跟她媽壹個性子。去吧路水文,忙妳的正事去吧。”
路波沒吭聲,兀自走了,臉上完全是事不關己的模樣,讓鄧朝露納悶,他怎麽這樣啊,都鬧成這樣了,還能打他的牌。
鄧朝露追上來,毫不客氣地問:“是不是妳操縱的?”
路波知道鄧朝露問什麽,不否定,但也不承認,仍舊走著,走幾步停下,瞅了瞅黑壓壓的人群,像是忽發感慨地說:“當年要不修這水庫,就沒這事了,世事難料啊。”說完,也不理會鄧朝露,壹個人往前走了。
鄧朝露越發覺得路波不大對勁,不只是樣子怪,說的話更怪,傻傻地望著路波背影,壹時竟有些恍惚,這人是路波嗎?聯想到路波近來壹連串古怪的行為,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傳聞,鄧朝露腦子裏冒出壹個疑問,路伯伯到底在玩什麽啊?
鄧朝露已經聽說,這些人早就是路波的常客,他們跟路波稱兄道弟,關系親熱得不是壹般。來了吃路波的,喝路波的,抽路波的,走時還順手牽羊,將水文站壹些七零八碎的東西拿走。在他們眼裏,水文站就是路波的。水文站的職工有意見,但礙著路波是元老,都不敢說。路波自己也不檢點,對這些人尤其縱容。他現在精力根本不在工作上,對站上的事想問了問幾句,不想問什麽也不問。幸虧副站長是位很敬業的同誌,事無巨細都替路波把心操了。上級念著路波是位老同誌,馬上到退休年齡,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反正現在工作就這樣子,沒誰真拿水文站當回事。
鄧朝露聽了,心裏越發不安。怎麽會這樣呢,在她心目中,母親他們這壹代人,沒有壹個不敬業的,工作起來個個玩命。就算是苗雨蘭阿姨,也是壹個工作狂。獨獨路伯伯,變成了這樣。
路伯伯這是怎麽了?
第三天,那個叫於幹頭的再來,鄧朝露就堵住了他。
“妳找我路伯伯幹什麽?”
於幹頭撓撓頭:“妳是小露吧,妳媽我們認識的,是管理處處長對吧?妳光屁股的時候,我還抱過妳呢。”
鄧朝露差點呸出壹聲,厭惡地瞪住這個人:“我路伯伯不歡迎妳們,這裏是單位,不是草原,妳們以後少來。”
於幹頭這才明白,鄧朝露截住他是為了表達不友好,而不是歡迎他,搓搓頭道:“這妳說了不算,我們找妳路伯伯是商量大事,大事妳懂不?不懂吧,關系到這條河,關系到整個流域。這事妳不用管,我們會奔走的。”
“奔走個鬼啊,我求求妳們,放過我路伯伯吧,他有病,經不起折騰。”鄧朝露眼淚都要出來了,這兩天她看到路伯伯在大把大把吃藥,咳嗽起來很厲害,每次吃飯都很少,夜裏也是半夜半夜地睡不著覺。昨天半夜他又在吹笛了,笛聲淒婉,直往人的心裏鉆,攪得鄧朝露根本就沒睡。
“嘿嘿,妳這丫頭,話咋這麽說哩,有些事妳不懂,甭看妳是研究生,社會上的事妳還真不懂。算了,不跟妳多說,妳路伯伯呢?我找他有急事。”
“他不在!”鄧朝露沒好氣地給了壹句。於幹頭並不介意,沖院裏“老路”“老路”喊了幾聲,路波就像壹頭老牛壹樣奔了出來。他們不願意讓鄧朝露聽到談話內容,又往聽山石那邊去。鄧朝露走過去,壹把拽住路波。
“憑什麽啊,不跟他們來往行不?”
“這妳不懂的,回去!”路波嚴肅起來。
“我不,我讓妳回去,不許跟他們來往。”
“亂說什麽,快回去。”路波臉色變得難看,不滿地看著鄧朝露。鄧朝露偏不,任性地站在那裏。這時副站長出來了,沖鄧朝露說:“到我辦公室去吧,我有話跟妳說。”
副站長不是本地人,華東水利學院畢業後分配到了祁連省,畢業時間跟鄧朝露差不多,鄧朝露讀研,他沒讀,現在也是祁連省水文領域的中堅力量了。他跟鄧朝露推心置腹談了壹下午,從河談到流域,談到流域這些年的治理,還有地方政府或省裏出臺的種種舉措,以及下遊和上遊不可調和的矛盾。兩人似乎有很多共同語言,看法也基本壹致。不過對流域的未來,鄧朝露充滿憂慮,副站長卻淡淡壹笑,很有信心地說:“壹切都會好起來的,只是時間問題。”
“官僚,妳們這些人就愛說官僚話。”兩人年齡差不多,副站長大鄧朝露幾歲,資歷也不相上下,鄧朝露在他面前說話相對從容壹些。副站長並不爭辯,這是壹個看上去城府頗深的人,心裏能藏住東西。他憂傷地捋了下頭發,話題落到了路波身上。他問鄧朝露,是不是對路波很失望?鄧朝露嗯了壹聲,副站長笑笑,說了聲別。鄧朝露問為什麽?副站長嘆壹聲,搖了搖頭,很是沈重地說:“我也說不清,看到站長那樣,我很自責,總覺得是自己沒把工作做好。”
“跟妳有什麽關系啊,妳替他做的已經夠多了。”鄧朝露不解地說。
“有些事沒有因果,有些事卻必有因果,路老師他心裏苦啊。”壹席話說得兩人都垂下頭去,半天,副站長說:“不要對站長有誤解,我雖然不知道他在做什麽,但我相信,他是正確的,他絕不是壹個自暴自棄自私自利的人。”
“正確?”鄧朝露驚訝了,站起身子,還以為副站長叫她來,是要商量辦法拯救路伯伯,沒想他居然說路伯伯是正確的。
“他正確在哪,就這樣天天跟這些人在壹起,妳看他現在過的這叫什麽日子!”
鄧朝露激動了,壹氣說了許多,言語中甚至有傷害的字眼出現。她詛咒那些穿戴不整的人,詛咒於幹頭也詛咒五羊,說他們是無賴,壹夥遊手好閑好吃懶做的人,是他們讓路伯伯墮落,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
副站長默默聽著,並不打斷鄧朝露。等鄧朝露說完,起身,望向窗外,望著對面茫茫的祁連。
良久,他說:“我們的目光還是太淺了,看不透這座山,看不透這裏的人,等著吧,他們或許會創造奇跡。”
鄧朝露聽得莫名其妙。回到路波辦公室時,路波睡了,他喝了不少酒,臉紅著,呼吸聲很重。再去看時,於幹頭他們已經走了,聽山石下壹片幹凈,什麽痕跡也沒留下。鄧朝露有些茫然,孤獨地坐在聽山石上,遠處的松濤聲傳來,轟擊著她的心。河水嘩嘩,世界進入完全陌生的狀態,鄧朝露忽然哭了,她不知道為什麽要哭,但她確確實實哭了。哭到後來,偏是又想起那個叫秦雨的人,想起自己死去的愛情。她幾乎要被痛苦淹沒了,感覺自己已被這個世界拋棄,誰也不在乎她,誰也不跟她講實話,誰也在拒絕著她欺騙著她。
這天黃昏,天將要黑下來的時候,路波非常鄭重地將鄧朝露叫到面前,跟鄧朝露談起了秦雨。這是路波第壹次跟鄧朝露談愛情,場面顯得神聖。愛情兩個字,在路波心裏的地位跟別人斷然不同,路波這輩子對什麽都無所謂,他過得隨心所欲,無欲無剛,臉上讓歲月這把刀深深地刻下壹蹶不振四個字,到哪都洗白不了,很難從他身上看到令人怦然心動的東西。獨獨對愛情,路波卻有頑固的眷戀和奉若神明的虔誠。鄧朝露對秦雨那點心思,路波早就知道了,所以沒點破,是想讓兩個年輕人自自然然戀愛,他等瓜熟蒂落那壹刻。人活著有愛情多好啊,再暗淡的人生也會因此而精彩,再虛弱的人也會因愛情而剛強。哦,愛情,每每看到有人相愛,路波自己先陶醉起來。沒想到這事突然有了變故,黃了,沒了,夭折了,半途而廢了,路波心裏不好受啊,感覺心上肉被人狠狠挖掉了壹塊。
鄧朝露起先躲閃著,不肯說實話,任憑路波怎麽問,只說哪有這回事啊,路伯伯,我跟他之間啥也沒有,真的沒有。路波急了,擡高聲音說:“小露妳別打斷我,伯伯就妳這麽壹個閨女,妳的心思伯伯懂,伯伯所以不提這事,就是不想讓妳難過。”
“我沒難過。”鄧朝露忽然捂住鼻子,不爭氣的鼻子,居然就酸酸地發起了澀,後來又忍不住發出壹片嗚咽。
路波心疼地伸過手,攬過鄧朝露的肩說:“不難過,小露不難過。”可他自己的眼淚卻下來了,竟然哭得比鄧朝露還恓惶。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麽傷害比愛情帶來的傷害更深重呢,沒有,路波堅信沒有。愛情可以讓壹個人幸福地活,活得奪目,活得燦爛,更可以讓壹個人死。他算是死過好幾回了,如果不是心中還藏著壹個結,怕是早就壹頭紮進雜木河了……
哭了壹陣,路波抹掉淚說:“小露,告訴伯伯,還有辦法挽救不,只要有壹線希望,伯伯就豁出去,為妳赴湯蹈火。”
鄧朝露感動地望著路波,這句話好溫暖哦,幾乎可以撫平她內心的傷。她堅定地搖搖頭,她不是那種企求別人施舍的人,更不是從別人手裏掠奪幸福的人。這點上她跟母親鄧家英是那麽得像,跟路波也是驚人的相同。他們三個,真是像壹家人哦,可惜不是。
“不,伯伯,您別枉費心機了,死去的東西再也不會復活,不會。”她咬住嘴唇,咬得嘴唇都已出血了。血從牙縫裏滲出來,滴在路波心上,路波的心銳利地疼了幾下,攬著她的手禁不住發抖。這是壹個多麽懂事的孩子啊,又是壹個多麽堅強的孩子,路波還怕她挺不過來呢,更怕她做出什麽荒唐事。
女人是為情生為情死的,這點路波非常堅信。路波幾乎就要欣慰了,可心的某個地方突然壹動,柔柔軟軟地那麽動了壹下,就又把他動得復雜,動得恍惚,仿佛心裏糾結著的那個結猛然要打開。他已經感覺到攬著鄧朝露的手跟剛才有些不同,傳遞出另外壹種力量了,慌忙間他將自己制止住。
不能啊,他聽到這麽壹聲,手陡然壹松,從鄧朝露肩上落下。
路波捂住了臉,壹股藏在心底很深處的淚噴出,差點將他淹沒,差點將他帶進另壹股洪流中。半天,路波平靜下來,變得不那麽神經。他沖鄧朝露笑笑,盡管勉強,但溫暖是顯而易見的。
“忘掉他吧,伯伯不忍心看妳這樣子。小露這麽優秀,還怕沒男孩子追,將來壹定找個白馬王子。”
鄧朝露撲哧壹聲笑了,路波這麽老舊壹個人,居然也能說出白馬王子。她仰起脖子說:“伯伯妳甭替我擔心,妳的身體要緊,以後不許喝酒,跟那些人還是少來往。”
路波淡淡地笑了笑,說:“他們是好人,伯伯信得過他們。”
“可我信不過他們。”鄧朝露頂了壹句嘴,轉而又甜甜地笑了。因為她看見明亮的笑已在路波臉上升騰起來。她這次來,不想給路伯伯心裏添堵,只要路伯伯開心,比什麽都重要。於是起身,高高興興替路波洗衣服去了。白天裏她還賭氣,路波臟衣服堆了壹堆,本來想洗的,後來故意裝看不見。這陣就笑自己傻,有些氣妳根本賭不出,也不該賭。路波癡癡地盯著鄧朝露的背影,盯著盯著,就又恍惚,不自禁地就又想起壹些事來,後來他嘆壹聲,回頭拿出相夾,壹遍遍撫摸。
鄧朝露本想在雜木河水文站多待些日子,她有個課題,需要石羊河近壹年的水文觀測數據,她想借這個機會,把數字整理全。副站長已經答應,讓站裏幾個年輕人幫她。誰知第二天,山下就出事了。當時鄧朝露正跟幾個工作人員翻觀測記錄,壹項項往表上抄錄數據,忽聽得門外響起尖厲的聲音,是那個叫五羊的,進院就喊:“老路,老路站長,快出來!”鄧朝露擡頭往外看,就見路波急急地走出辦公室,跟五羊在院裏嘀咕幾句,然後坐上五羊的摩托車走了。鄧朝露感覺不大對勁,追出來,路波他們已沒了影。正生著氣,身後響起副站長的聲音:“走吧,今天壹定有熱鬧看。”
鄧朝露坐著站上的車,跟副站長他們壹同到了離水文站十公裏遠處的南營水庫。這是石羊河從源頭數起的第壹座水庫,雜木河還有紫水河以及南部山區的幾條河流在南營前面的貢達梅嶺匯合,然後滾滾而下,要穿過雄險的野鹿谷時,突然被壹座大壩攔住,這大壩就是南營水庫。
這座水庫跟西邊另壹條支流上的西營水庫、東邊黃羊河的黃羊水庫構成石羊河第壹道防護體系,活生生地將奔騰的河水給攔斷。也正是憑了這三座大壩,上遊谷川區才儼然成為河的主人,像是掐住了河脖子,總是顯得底氣比別人足。鄧朝露他們趕到的時候,下遊龍山和沙湖的人剛剛跟南營這邊的群眾打完架。兩邊來的人都不少,尤其南營,近乎把半個鄉的人都發動了上來,黑壓壓地站滿了大壩,兩邊山坡上也是。而龍山和沙湖那邊自然就顯得力量單薄了些,他們來了三卡車人,是來搶水的。
鄧朝露急著找路波,生怕路波攪進是非中。副站長讓她別急,壹再說路所長不會的。可他顯得比鄧朝露還急,已經不停地跟別人打聽路波的下落。圍過來的人很多,七嘴八舌都在說剛才打架的事。有人說打得很兇,龍山那邊兩個人斷了胳膊,另壹個被打斷了三根肋骨。也有人說屁事也沒,都在幹吼卻不動手。說這話的人中就有於幹頭他們。他們看上去幸災樂禍,幾個人圍在壹起抽煙。那煙肯定又是路波賞給他們的。鄧朝露心裏就想,這架跟路波有關,壹定是他在背後教唆,讓於幹頭們挑弄是非。後來得到的消息果然如此,路波充當了幕後教唆和操縱者,於幹頭們不過是他的“幹將”。往下遊調水是谷水市早就做出的決定,鄧朝露他們在沙湖縣搞完那次科研,谷水市的決定就做出了。上遊谷川區卻堅決不答應,幾次協調都沒成功。但下遊旱情壹天重過壹天,不只是莊稼,樹也成片成片地渴死。沙湖縣幾度告急,孔縣長擺了好幾次酒宴,就為了讓谷川區的領導點個頭。可這個頭點起來實在困難,大家都盯著這點可憐的水,盯著這條可憐的河,僧多粥少,顧及不到啊。僵來僵去,市裏發了火,強行要求上遊谷川區開閘放水,解下遊之困。誰知開閘第壹天,就遇到了上遊群眾的圍攻。
南營鄉幾千號人站在大堤上,打著橫幅:人在水在,誓與河水共存亡。下遊沙湖和龍山的群眾也打起了橫幅:壹河所生,壹河所養,有難同當,有福共享。有人甚至打出了“娘的奶頭妳吃得我也吃得”這樣直白的標語。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區裏和縣裏的領導都被叫去,谷川區長不講話,只是說只要群眾答應怎麽都行,我們沒意見,都是壹河水養大的嘛。龍山縣長說這不是明擺著推責任嗎,群眾說了算還要領導幹什麽?谷川區長笑說,依靠群眾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這個傳統什麽時候都不能丟。龍山縣長明知人家是在搪塞,不想解決問題,但又在語言上占不了優勢,只能焦急地看沙湖縣長孔祥雲。反正沙湖旱情比龍山還重,只要沙湖能度過去,龍山就能度過去,好歹龍山還有幾座水庫呢。孔祥雲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他以前在谷川做過常務副區長,去年才調到沙湖縣。上遊情況要說他比龍山縣長更了解,三座水庫的水充其量也只能解決谷川自己的問題,但他現在是沙湖縣長,就不能這麽想問題。他站出來說:“聽群眾的沒錯,但這條河不是谷川區的吧,祁連山不是谷川區的吧,上遊要豐收,總不能把下遊餓死,怎麽著也得分壹瓢給下遊解渴。”
“水就在庫裏,我沒藏起來,兩位縣長要多少,只管拿走,我絕沒意見。”谷川區長依舊不急不躁地說。
“怎麽拿?妳讓水庫工作人員躲起來,大壩又讓群眾占著,我們怎麽拿?”龍山縣長咄咄逼人道。剛才是群眾吵架,這陣輪到他們吵了。谷川區長卻不想吵,做出壹副甘拜下風的樣子:“我的兩位好領導,千萬別冤枉我,水庫管理人員是讓群眾趕跑的,情況妳們都看到了,再鬧下去,我這個區長也會讓他們趕跑。”
“裝,裝,裝,妳就裝。”龍山縣長明知谷川區長是在演戲,卻又拿他沒辦法,這事攤誰頭上,怕都壹樣。去年沙湖縣跟他告急求援,他壹樣裝了啞巴,壹滴水也沒支援。沒想到同樣的難題現在又擱到了自己頭上。
三位領導都是位子上的人,平時見了壹個比壹個熱情,壹個比壹個客氣,禮尚往來,客套得很。這陣為了水卻要紅臉,也實在是難為他們。
市委書記吳天亮壹直看著三位,他是中途趕來的,他來的時候,三方群眾正糾纏壹起,中間確也動了手,不過還算克制,沒出大問題,傷的幾個人他看過,都不重。本來他想把公安叫來,後來壹想算了,集體突發性沖突面前,還是保持克制的好。
“說吧老陸,這水到底放還是不放?”吳天亮問谷川區長。
“書記,您也看到了,群眾情緒這麽大,我真是無能為力啊。”谷川區長姓陸,聽見吳天亮問話,苦著臉說。
“我看妳根本就沒想著解決問題,煽動群眾情緒,鼓動鬧事,老陸妳膽子不小啊。”吳天亮拉下臉來批評。陸區長結巴著,他還沒膽子讓吳天亮生氣,但他真沒能力說服外面的群眾。正尷尬著,吳天亮開口了,他沖孔祥雲和龍山縣長說:“先把人帶走,其他問題回去再解決。”兩位縣長面面相覷,極不甘心,但市委書記這樣說了,他們也沒辦法,只能服從。
陸區長倒是松下壹口氣來。
吳天亮又轉向市委秘書長:“路波找到沒,等他多長時間了?”市委秘書長結結巴巴說:“站上說他早就出來了,但現場找不到他。”
“打電話給鄧家英,讓她去找!”吳天亮火了。
這個時候,鄧朝露正在四處找路波。水庫上到處是人,黑壓壓壹大片。有的在看熱鬧,有的在等待更大的熱鬧,更多的,卻是在嚷嚷著水。鄧朝露步子飛快地穿來穿去,哪也不見路波的影子。她問過幾個熟悉的人,都說沒看到。後來她看見幾個跟洛巴穿戴壹致的藏人,想走過去問問他們。那些人站在半山腰間,居高臨下地俯視著這些為水吵得不可開交的漢人們。山腰上不知什麽人在唱《五哥放羊》,嗓子還不錯,淒淒切切的聲音跟山下水庫上正發生著的事很不和諧。鄧朝露剛到山腳下,就聽有人說,路波正跟幾個放羊的老漢“挖牛”呢。
“挖牛”鄧朝露懂,是壹種類似撲克牌的玩法,山裏人管壹種紙牌叫“牛九”,閑時沒事,就靠它打發光陰。鄧朝露走過去,見山腳壹背風處,幾個老漢坐在皮襖上,面前攤開壹張羊皮,路波就在中間,手裏抱著“牛九”牌,正笑瞇瞇地計劃著怎麽讓幾個老漢輸掉。幾個老漢壹看就是行家裏手,根本不服他。有個老漢聲音很大地訓他:“磨蹭什麽,出牌啊陸水文。”
“三老虎!”路波猛叫壹聲,甩出三張Q來,老漢哈哈壹笑,臉上露出得意道:“就知道妳舍不得牌,打對老虎我就輸了,三牛!”路波懊惱地連叫幾聲,騰地起身說:“不玩了不玩了,玩不過妳們。”
壹股子塵騰起,是路波屁股上的土。老漢們不依,剛才贏了牌的叫囂:“正玩興頭上呢,不能走,人家搶水妳慌個啥,去搶好了,反正水遲早要幹掉。”
“誰說的?!”鄧朝露奔過去,不滿地瞪了老漢壹眼,壹把拽過路波:“找妳都找瘋了,還有心思玩?”
“找我做什麽?”路波明知故問。老漢幫腔道:“這是鄧家女子吧,嗯,長大了,長成野丫頭了。”
“妳才野丫頭哩。”鄧朝露學著山裏人的話,搶白了壹句。幾個老漢馬上笑了,都說:“像,跟她媽壹個性子。去吧路水文,忙妳的正事去吧。”
路波沒吭聲,兀自走了,臉上完全是事不關己的模樣,讓鄧朝露納悶,他怎麽這樣啊,都鬧成這樣了,還能打他的牌。
鄧朝露追上來,毫不客氣地問:“是不是妳操縱的?”
路波知道鄧朝露問什麽,不否定,但也不承認,仍舊走著,走幾步停下,瞅了瞅黑壓壓的人群,像是忽發感慨地說:“當年要不修這水庫,就沒這事了,世事難料啊。”說完,也不理會鄧朝露,壹個人往前走了。
鄧朝露越發覺得路波不大對勁,不只是樣子怪,說的話更怪,傻傻地望著路波背影,壹時竟有些恍惚,這人是路波嗎?聯想到路波近來壹連串古怪的行為,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傳聞,鄧朝露腦子裏冒出壹個疑問,路伯伯到底在玩什麽啊?